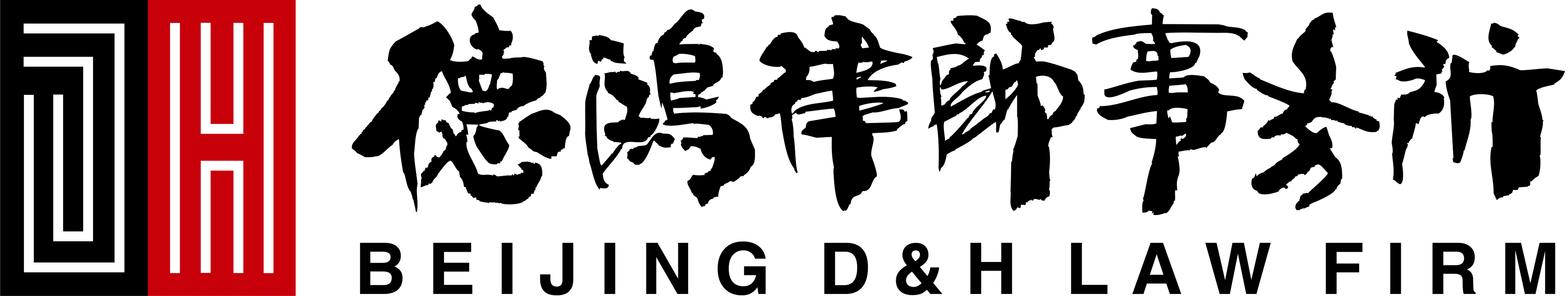日前,笔者代理了一案件,简要案情如下:2014年甲与乙结婚,2016年乙以其名义向A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而获得该A公司的股权,2017年乙与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乙将其对A公司的股权以0元转让给丙,之后A公司办理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丙成为A公司的股东。2022年1月,甲向法院起诉乙和丙,要求法院认定乙和丙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丙需向乙和甲返还股权,理由是《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的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乙的转让行为为无权处分,此时甲与乙仍是夫妻关系,没有离婚。
作为被告丙的代理人,笔者认为该案件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一、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对外投资所取得的股权(为简述,下文统一简称该股权)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二、夫妻一方对外转让该股权的合同何种情形下会被认定为无效?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查阅了一些文章和司法案例,归纳总结如下:
一、关于该股权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
就此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尽管各方都认可我国的夫妻共同财产制是指婚后所得共同制,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所得的财产,除另有约定或法定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外,均为夫妻共同所有。但对于该股权是否为共同财产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股权是财产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夫妻一方所获得的股权当然也是夫妻共同财产,且是不分份额的共同共有。夫妻双方对于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对于非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分时,双方应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未经协商,任何一方擅自处分,均属于无权处分,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相对人符合善意取得外,因此夫妻一方股权的转让亦应遵守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该股权在出资财产来源上是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出资或受让取得的,但该股权不能也不应简单一概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形下,可以认定该股权及其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若涉及第三人时(如对公司行使股权、股权转让等)则另当别论,因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而是股东在兼备人合与资合法律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基于股东资格或地位享有的权利总称,除具有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就该股权的行使与处置,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对外行使或处分该股权时,股东本人有权依据《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进行,因此,夫妻一方对外投资所取得的该股权,非登记为股东的一方对外是不能够主张该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而仅能主张该股权所带来的收益和代表的价值利益为夫妻共同财产。
第三种观点认为,不管是否涉及第三方,该股权均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只是该股权所带来的收益和代表的价值利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由与上面第二种观点中涉及第三人时对股权定性的观点相同。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对该股权的归属认定也存在不同观点,部分法院认为只要是在夫妻婚姻关系期间用共有财产投资取得的股权都应是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2民终4484号民事案件、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4民终3040号民事案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民终957号民事案件、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7民终5298号民事案件、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9)吉0204民初2029民事案件等裁判文书都认定该股权为夫妻共有财产,夫妻双方对该股权有平等的处理权。
部分法院认为股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该股权所带来的收益和代表的价值利益为夫妻共有财产。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4023号民事案件、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苏04民终840号民事案件、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2民初45744号民事案件、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4民终386号民事案件等判决书均认定股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股权所代表的财产利益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由多是从公司法相关法律规定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我国公司法不认可股权共有,同一股权不能同时登记在两个人名下;其次,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资二合性,决定了股权是一种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权利,该股权中具有人身属性的权益,因此该股权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就应归该一方享有,该一方对该股权享有独立处分的权利,且公司法规定股东转让股权本身可以独立行使,无需征得其配偶的同意,也没有法律规定股东转让股权需经股东配偶的同意;再者,我国《民法典》或之前的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只规定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配偶一方可以享受对方所得的收益,但未规定其可分享收益的权利基础或身份。因此股权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股权收益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有些法院的裁判文书则在涉及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中,不直接论述股权是否为夫妻共有财产,而明确“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应适用我国合同法、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权流转方面,合法转让主体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且股东转让股权须经其他过半数股东同意,而非必须征得其配偶的同意。”如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2民终1677号民事案件、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鲁14民终4110号民事案件、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20)粤18民终1907号民事案件、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4民终1200号民事案件等判决书均以相同理由裁判。
2021年4月,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了《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会议纪要(第二辑)》,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2020年第3次法官会议中明确了“股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身份和地位而在公司中享有的权利,包含资产收益权、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兼具财产权与人身权属性。根据《公司法》规定,取得完整无瑕疵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应同时符合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这一实质要件和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等相关文件这一形式要件。换言之,出资并非取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充分条件,不能仅因出资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认定该股权为夫妻共同共有。当股权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时,该股权的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股东有权单独处分该股权。”这个会议纪要解决了出资来源导致权属纠纷的问题(不仅是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也包括了家庭共同财产出资等),对统一司法审判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夫妻一方对外转让该股权的合同效力
通过检索并分析相关司法审判案例,发现法官的审判思路基本是,若认为该股权非夫妻共有,夫妻一方有权处置其名下股权的,此时仅需分析转让行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等法定无效情形,若无则有效,若有则无效;若认为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当转让行为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根据《合同法》中无权处分的相关规定,若符合善意取得且没有法定无效情形时转让合同有效,否则无效;当转让行为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后,只要转让行为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则有效。
由此在《民法典》实施之前,若按照无权处分审理股权转让的纠纷案件,法院一般会从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的了解熟悉程度及关系、受让人是否了解转让人的婚姻状态来判断受让人的主观性,断定是否符合善意取得,以及是否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无效情形。若转让双方是朋友同学或亲属等亲朋好友关系,则法院一般会认定受让人应知或明知该股权是夫妻共有,非善意人,如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在(2019)吉0204民初2029号民事案件,首先认定该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一方未经配偶同意将案涉股权转让侵犯了作为共同共有人的权利,属于无权处分;然后认为受让人作为职业经理人在公司营业多年,且与转让人是同学关系,应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其明知该涉案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转让人故意不通知配偶转让该股权的情况下,其仍与其进行股权转让,在此情况下受让股权难谓善意;再者,结合交易双方特殊身份关系及交易后转让人提起离婚诉讼的特殊背景,应当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就股权之转让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因此转让合同无效。若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可被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而认定无效,如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7民终5298号二审民事判决书认定:江文慧与聂隆健凯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双方因此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聂隆健凯以0元的价格将赣州畅有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江文慧,实质是赠与行为。该行为侵害了罗昭君的共同财产权,且违反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于《民法典》施行后发生的该股权转让行为,法院一般从是否符合我国《公司法》中有关股权转让的法律规定、《民法典》中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予以考量,只要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即有效。如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2)苏04民终840号民事判决书中论述“本次转让期间又正值薛峰与符娇娜离婚诉讼期间,周兰华作为薛峰的母亲,对于薛峰与符娇娜之间的夫妻感情情况理应知晓,本次转让却以0元股权价值的形式转让,结合本次转让的时间、双方之间的关系、对价支付等因素,本院难以认定周兰华接受本次股权转让的过程为善意,现亦无证据表明符娇娜对本次转让是同意并知晓的,故本院有理由认定薛峰与周兰华之间转让常晨雨公司股权的行为损害了符娇娜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无效”。其他法院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3民终11848号民事案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民终957号民事案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2民终4484号民事案件等判决书中的说理相似。
同时笔者注意到,在考量转让双方是否有恶意串通情形时,法院对受让人的主观无恶意性的审查更严格,除了积极行为外,还认为即使受让人在主观上不属于积极追求,但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的态度,亦属主观故意范畴,并考量受让人是否履行了最基本的询问与注意义务,如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2民终4484号民事案件中,法官认为“退一步分析,即使存在极端情况,冯立国确对杨雪已婚与否不知情,但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杨雪早已过而立之年,冯立国作为无偿取得财产的受让人,其亦应对该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转让是否可能损害他人合法权利尽到最基本的询问与注意义务。但从本案现有证据分析,始终未见冯立国尽此义务以避免损害结果发生,而是径行签订合同并无偿受让财产。由此可以认定,对于王永民财产权益的损害结果,冯立国在主观上即使不属于积极追求,亦属于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的态度,亦属主观故意范畴。据此,对于杨雪与冯立国存在恶意串通情节的事实,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行为损害了王永民的合法权利。”
当然,在认定转让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情形后,还需要证明该转让行为是否会造成他人利益的损失,若没有造成损失,则不认为是恶意串通而认定转让合同有效,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再482号的再审民事判决书认定:无论钟发秀将大丰水厂权利转移至谁的名下(包括其子钟翔宇、郝玉林、李瑞林),只要遵循市场交易原则,遵守法律规定,不损害利益相关人的权益,法律都是允许的,不能仅以交易对方来判断交易是否合法,最终落脚点仍是转让价款。根据法律规定,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包括:(1)双方行为人是否有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恶意,即明知某种行为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故意为之;(2)行为人双方存在事先通谋,即双方都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损害第三人利益。因此,构成恶意串通的最终条件是第三人即本案中的陈年勋利益受损,而前文已经对此进行了论述,在股权交易价格相当于或高于股份价值的情况下,陈年勋的利益不会受到任何损失,陈年勋所举证据不能证明钟发秀与郝玉林转让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因此,陈年勋要确认钟发秀与郝玉林之间签订的《水厂股份转让协议书》转让协议无效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该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
综上,通过对司法审判案件的梳理,笔者对代理的案件有了一个较清晰的代理思路,首先,要论证并说服法官认可该股权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有权独自将其名下的股权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进行转让;其次,证明该股权转让双方没有恶意串通,包括对该股权转让的背景分析,转让价为0元的理由,为什么要转让给丙而非其他人;再次,证明该股权转让给丙后并没有损害甲的利益,反而通过股权价值的提升给其增加了丰厚的收益,这可通过包括公司财务报表中相关指标的变化、股权所对应利益的增加、对公司经营状况所带来的益处、吸引投融资机构的投资、准备上市等材料来证明;最后是证明不存在其他法定无效情形。
目前,该案正在审理当中,后续结果笔者将另文分享。